
一年前的这段日子,我打破了很少触碰“危险题材”的禁忌,连续写了几篇文章。意外的是,不少技术圈的朋友都给我发消息表示支持。于是我知道了,不管在哪里,不管多阴暗,只要出现一点微光,总会有人看见。
发出一点微光,听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,做起来却并不容易。在正午发出一点微光,简单却似乎毫无意义,在子夜发出一点微光,振奋但需要不小的勇气。尤其是今天,似乎没有谁的工作内容就是“发光”,而大家又都背负着很大的生活压力,所以,在本职工作之外,还能发出一点微光,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怎么办呢?我的办法是,多读点书,多从其他人,尤其是普通人的故事里获得启发和力量。所以今天,我想谈谈最近看过的两本书。
一本是美国人列斯特·坦尼的《活着回家》,这是一本自传,叙述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军官兵,如何在日军战俘营里度过了非人的岁月,最终“活着回家”的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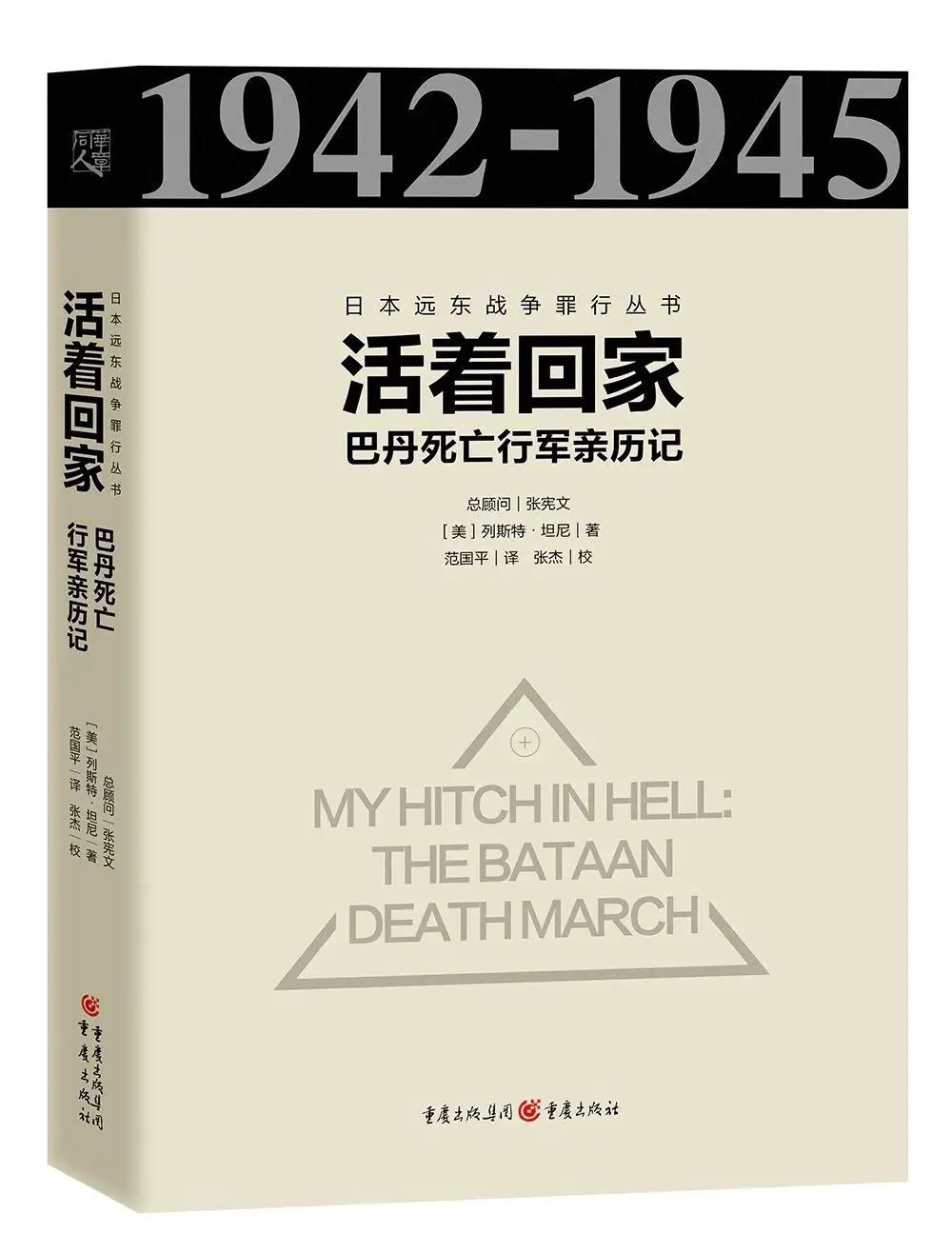
如果你之前没听说过“巴丹死亡行军”,或者仅仅听说过这个名字,但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,那么坦尼的回忆绝对可以极大丰富你的认知——在热带的暴晒之下,成千上万的美军战俘,衣衫破烂、步履蹒跚,每天被强迫长时间行军,连喝一口水都成了奢念。终于有一天许多人实在忍不住了,直接扑向路边牛羊洗澡的水塘,张大口喝下墨绿浑浊、腥臭难闻的“水”,结果,绝大多数人要么被日军枪杀,要么陆续病倒。
即便是行军结束,进入战俘营,待遇也不见得有所好转,等待他们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,和无处不在的刑罚——已经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军认定,“黄种人已经被白种人欺负了那么久,现在风水倒过来了”。有战俘因为体力不支倒下,也有战俘因为受不了精神的折磨而倒下。
《活着回家》的作者之所以能幸存,一方面是他的信念很坚定,相信自己一定能“活着回家”,另一方面也是他能屈能伸,他是极少数愿意“屈尊”学日语的美军战俘(尽管后来他发现自己学的日语很粗鲁,因为分配来战俘营的日军都出身社会底层)。因为他学会了日语,日军对他有所依赖,他也能和一些心怀同情的日军士兵建立交情,得到了照顾和同情——这让我想到张泽石的《我的朝鲜战争》,同样是在战俘营,同样是努力去学习其他人的语言,同样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。
不过纵观全书,让我印象最深还是两处“微光”,即便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,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。
其一是在菲律宾,日本士兵押送坦尼运送金属废料的途中,在路边的菲律宾人小店里买些水果。店主见到他们,特意从柜台下面拿出来五个新鲜的大红苹果,日本兵很高兴,花2个比索买了其中一个。
这个苹果虽然与坦尼无关,但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鼓舞:日本兵看不出来,那五个苹果并不是菲律宾本地的品种,而是美国特有的红苹果。这大概是一个游击队的据点,老板这么做的意义很清楚:国家没有忘记被俘的战士,一直在关注着他们。
在后来的岁月里,柜台上摆着五个红苹果的画面,一直支撑着坦尼,撑过了无数难熬的日子,最终回到祖国和家人的怀抱。
其二是在战俘营,各种物资紧缺,大多数人都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。但是美军战俘休利特医生偷偷告诉坦尼:他希望为战俘制作一份病历。
休利特医生的理由很充分:虽然目前缺医少药,但大家都不可能在战俘营里呆一辈子,总有一天要获得解放。到那个时候,有了病历,有了翔实的医疗记录,医生就可以为每一个人制定更准确的方案,帮助大家恢复健康。但是休利特的要求也很难满足:在战俘营里,任何“多余的物资”都有巨大的风险,极难获得,何况是和生活保障无关的纸和笔。况且,保存这些记录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,而不会有任何任何现实的好处。
不过休利特医生的决心很坚定,坦尼也非常理解,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,费尽了周折——先弄到牙膏,再用牙膏换烟草,最后用烟草换来纸和笔。但是,无论是休利特还是坦尼都预料不到,战后对于退伍军人管理局来说,这份战时医疗记录有多么重的分量。
另一本书是Greg Mitchell的The Tunnels: Escape under the Berlin Wall and the Historic Film the JFK White House Tried to Kill(隧道:柏林墙底下的逃脱行动,和肯尼迪政府尝试叫停的纪录片),这是一本叫人眼界大开的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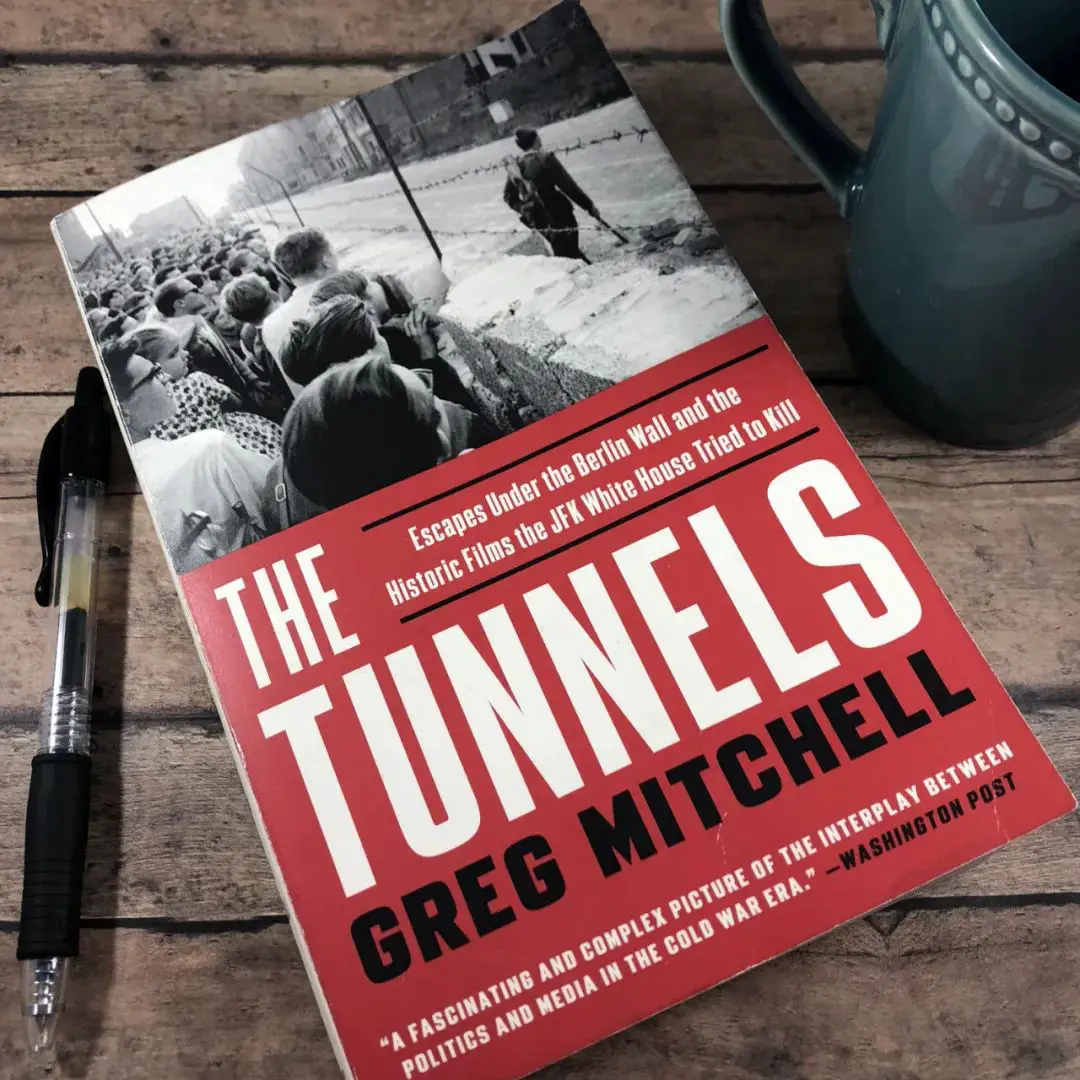
关于“翻跃柏林墙”,逃脱东柏林的故事,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。不过这本书讲的却是相反的故事:在柏林墙建立起来之后,西柏林有许多人摩拳擦掌,希望打通前往东柏林的隧道,营救自己的家人和同胞。
可惜,无论是从西向东的掘进,同样是风险重重。在墙的那一边,东德边防警察严防死守,秘密警察(史塔西,Stasi)随时监视着任何可能逃脱的人,为了保密,逃脱者往往只能在逃脱之前一两天得到消息,然后要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;在墙的这一边,且形势之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,首先需要找到可信的愿意挖掘隧道的同伙,同时要提防无处不在的史塔西密探;为了筹措经费,一些掘进者选择了让NBC、CBS之类的媒体拍摄掘进过程作为纪录片素材,以此获取报酬,但此举又引起了其它掘进者的异议;美国政府得知此类拍摄计划之后,为了避免激怒苏联,导致冷战局势失控,极力劝阻电视台播出纪录片,但又不能触碰“破坏言论自由”的红线;西德官方也得知了此类计划,他们一方面希望看到更多成功的逃脱行动,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些行动被作为商业媒体的素材……
书中详细描述了三次逃脱行动,一次成功,两次失败。同样,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三次逃脱行动中的一个片段。
那是1962年11月14日夜里的逃脱行动。本次逃脱行动由前东德著名自行车运动员赛德尔(Seidel)主导,他和妻子早已逃脱成功,但他念念不忘要救出自己的母亲,所以积极参与到隧道掘进中来,并在逃脱行动的当晚自告奋勇,打破对妻子“永远不做第一个出隧道的人”的承诺,率先前往东柏林的隧道出口接应——虽然他已经知道,自己在东德政府的重点关注名单上。
不幸的是,这次逃脱的成员早已被史塔西渗透,行动早已被史塔西得知。除了守株待兔,史塔西更早早在隧道穿越边界的上方埋好了炸药,2.5公斤TNT,再加2.5公斤黑索金(高能炸药),足够把隧道炸塌,附近的房屋也难以幸免。对史塔西来说,误伤不重要,反而恰恰是他们所期望的,这样就可以作为栽赃宣传的材料,证明西德“破坏分子”的险恶。
第一个钻出隧道的赛德尔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史塔西的俘虏,第二名掘进人员鲍里斯刚刚钻出隧道,就听到赛德尔大喊:快来,我们需要帮助一个病人!
隧道里的人迅速意识到不对,以逃脱行动的保密要求,绝对不可能有人大喊,一定发生了什么。正在他们议论之时,赛德尔叫起来:快跑,有人告密,当兵的要开枪!
恼羞成怒的史塔西迅速把赛德尔拉到房间里(迎接他的是一顿毒打),同时现场的指挥官莱布霍兹(Leibholz)命令引爆,炸塌隧道,防止“破坏分子”逃回西柏林。
负责引爆的是国家安全部的爆破专家理查德·施梅恩(Richard Schmeing)中尉,他的业务非常熟练,也深得组织信任,但是在那一刻他犹豫了。因为他看到就在距离炸药不远的地方,夜色中有两个年轻人在拥吻,刚刚看完电影回来的他们,浑然不觉危险近在咫尺。如果引爆炸药,他们必然尸骨无存。施梅恩早年曾经从纳粹集中营幸存,这段经历大概让他比普通人多了几分恻隐之心,于是他抗议说:“那里有对年轻人。”
但是他的抗议只换来另一次的“引爆”,而且是以不容置疑的口气。无可奈何之下,施梅恩按下了引爆按钮。
但是,什么也没发生。
施梅恩又一次按下引爆按钮,仍然是一切宁静。
史塔西气急败坏地大喊:“猪逃掉了!”
这次行动,虽然史塔西抓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人物赛德尔,但这也只是他们全部的收获。更多的“破坏分子”没有抓到,更让他们恼火的是,炸药经常没有引爆,尽管新闻稿都已经准备完毕。事后检查发现,引爆线早在行动之前就被人用钝器或者玻璃碎片割开,然后用力拉断。在此后数十年里,史塔西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追查罪魁祸首,但是一无所获。
所以,大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谁切断了引爆线。不过,切断它的那个人大概也不知道,他的行动,不单挽救了隧道里的那些人,还额外挽救了夜色中拥吻的两名无辜的年轻人,更挽救了施梅恩的余生——他再不用接受组织的纠缠,也再不需要背负良知的债务。
时光机

如果喜欢本文,欢迎长按识别二维码订阅
